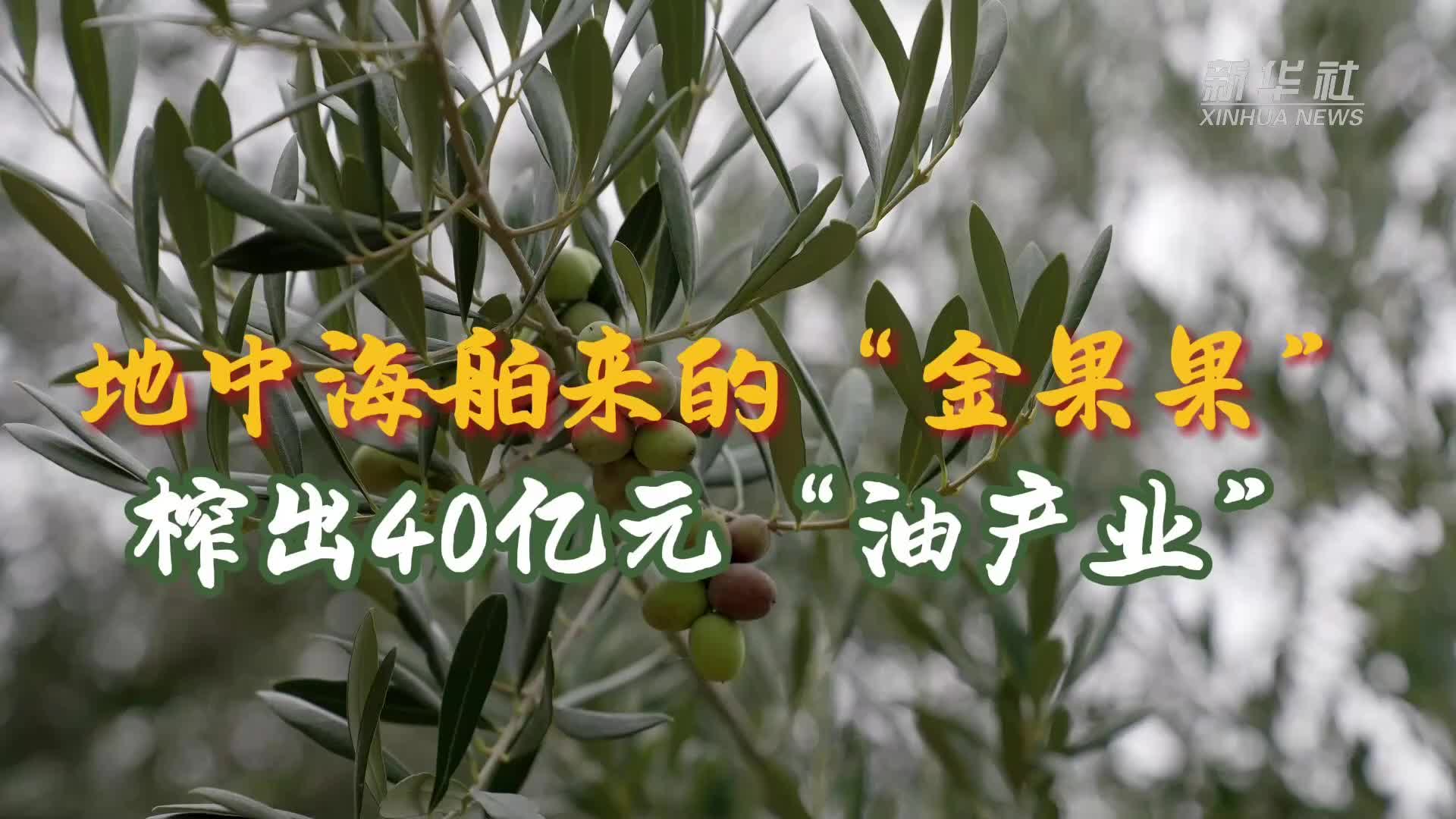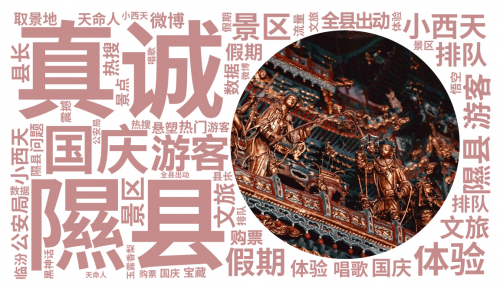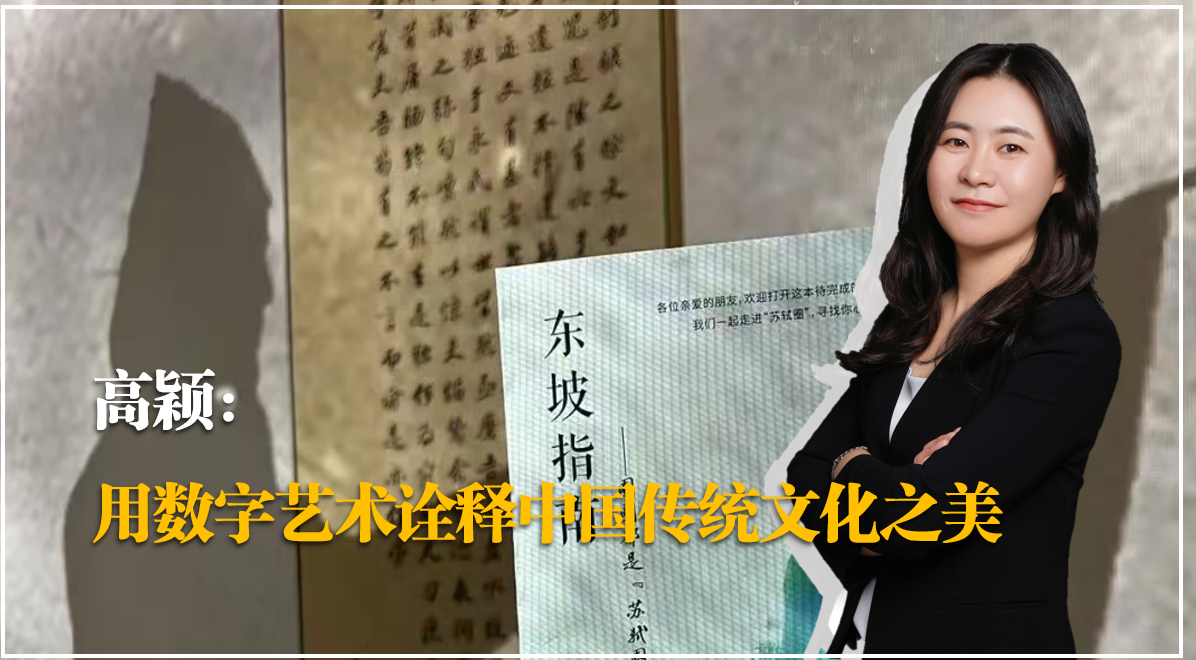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及民俗遗产化进程的推进,村落民俗博物馆应运而生,其展示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物质民俗遗存。作为乡土精神和传统民俗文化的新型载体,民俗博物馆以较强的社会工具性逐渐成为对外展示村落民俗传统、对内凝聚向心力的重要文化场所,对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现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龙泉村的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为例,通过田野观察、与村民及参观游览者的访谈等方式,呈现该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兴建历程、实物展陈、村民的参与及认知情况等。通过微观叙事展示村民熔铸在民俗之“物”中的文化,尝试分析村民如何通过共享的物质遗存、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存的村民自我表达与共生的宏大叙事联结凝聚出新的共同体。
博物馆起源于人们的收藏意识,人类学家逐渐关注博物馆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探寻如何利用博物馆的展品来展示文化,并对物质文化的内容进行反思,从而形成博物馆人类学这一学科分支[]。国际博物馆协会提出新博物馆学,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人”与“物”的关联中,关注民众日常生活,强化社区的参与[]。学者们也不断思考创新博物馆文化的展现形式,民俗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等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形式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我国建立了第一座村落地方专业性民俗博物馆——山西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层实践及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各地的村落民俗博物馆大量涌现。
学术界对民俗博物馆的研究主要基于人类学、民俗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学科。其中,人类学和民俗学关于民俗博物馆的研究成果丰富,高小兰、邹明华、伍晶等人对民俗博物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空间进行了研究。李佳、庚华等人研究了民俗博物馆在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和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中的价值和作用。谢奇伶将民俗博物馆作为文化记忆空间进行研究。魏文静、李晓芳、孙金惠等人将民俗博物馆作为旅游资源进行研究。戴亦佳、黄雪薇、祝琳琳等人将民俗博物馆作为乡村文化景观进行研究。倪明、罗玉鑫等人对民俗博物馆的艺术设计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民俗博物馆在设计方面对村落建设的价值,并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产出。
近景: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深描
龙泉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胜街道,有“贺兰山下第一村”的美誉。其地处大武口区南部,西依贺兰山,东临110国道,因村内有9个天然泉眼而得名。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龙泉村村域面积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1800亩,辖4个村民小组,人口355户,共1164人。2011年,龙泉村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全国文明村镇”;2018年,依托宁夏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龙泉村大力发展旅游业,全年接待游客超过14.7万人次;2019年,龙泉村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2020年,龙泉村游客接待总量达106.4万人次,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在有序规划的旅游开发中,龙泉村逐渐建成了完善的旅游基础配套体系和产业联合体系;同时还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的民俗资源,使其在村落旅游中充分彰显价值。
村民访谈资料显示,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于2008年7月开馆,资金来源主要是村集体经济资金和文旅局项目支持资金。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策展理念的确立和展陈设计主要由官方和民间力量共同协商、参与完成,馆藏的物质民俗物品,一部分来源于龙泉村村民的无偿捐赠,另一部分则是由地方文化和旅游局派送,体现了两种力量的联结与互动。
中景:民俗博物馆的文化意义阐释
(一)共享的物质遗存
弗朗兹·博厄斯在《民族学博物馆与其分类方式》一文中提到:“环境既包括自然,也要考虑周边族群,因此相关陈列也必须兼顾自然与人文,这也是唯一能展现出某一现象的特征与周边环境的方法。”[]在民俗文化博物馆内展示的用于整地、种植、收获等的农耕用具,因其体量较大,需要村民合作或是人力和畜力合作进行使用。它们以实物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龙泉村在特定时代的农业生产状态、村民的劳动方式及制作技艺水平。“无数普通俗凡的民具不仅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物证,还承载着中国亿万群众的生活智慧和情感,因此,理所当然地,民具应该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实践,龙泉村传统村落的文化类型及村民的物质生产生活民俗得以呈现,而这些特定区域及在特定时间中村民共享的物质遗存,对今天龙泉村村民的文化认同及社会关联乃至凝聚力都产生着积极的作用。
(二)共同的集体历史记忆
共同的历史记忆以物质为载体,康纳顿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和个体一样具有自己的记忆,并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的方式实现其保护和传递”。
龙泉村的第一任赤脚医生,今年已经77岁了。他从25岁开始做赤脚医生,回首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期这段时间,做赤脚医生是特别艰苦的。有时候人们在沟里放羊突然生病了,赤脚医生就得骑着骡子,背着药箱去看病,不分白天还是半夜,只要有人叫出诊,就背着药箱子过去。
作为记忆共同体的龙泉村村民有着生活上、思想上的共同记忆,在民俗博物馆中通过物品的展陈将历史遗存和村民记忆有效联系起来,村民由此形成了村落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记忆。这种方式和载体也是记忆延续和传承的内在要求,是保持记忆完整鲜活的重要方式。
(三)共建的村民自我表达
民俗文化博物馆集中展示了龙泉村村民的物质文化遗存,村民对器物的处理、保存、展示的方法和技术,器物与社会结构、村落组织、艺术审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解读,都体现与反映了村民的集体记忆和自我表述。
据村民介绍,龙泉村建设民俗博物馆,一是为了展示农村的变化,农业运作方式的转变,比如在婚姻方面,原来娶亲是用毛驴,现在都用小轿车;在农耕方面,原来是二牛抬杠式,现代都是机械收割,民俗博物馆也是村民们纪念的场所。二是起到了一定的教育的作用,例如评比好的家风家训,对村民的思想进步起到了激励和鼓舞的作用,同时也对后代的教育起到了良好的左右,让年轻人明白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旅游循环凝视下,东道主利用地方经验,不断更新本土文化,塑造出适应现代社会的乡村新文化,巩固文化自信的内生机制。”[]龙泉村村民以民俗文化博物馆为载体,在政府的引领和游客的凝视下,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实现平等的自我表达。
(四)共生的宏大叙事联结
博物馆作为一种重要的阐释和沟通媒介,通过收藏与展示连接过去与现在。村民通过物的展示参与到宏大叙事中,建立起村民与村落、农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博物馆展陈的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村民的生活用品和奖章证书等物品就体现了这样的文化意义。例如,在村史馆中展示张怀生、张怀英、高发成三位抗美援朝英雄的生平事迹,在民俗文化博物馆珍藏老兵们的军帽、奖章、徽章等物品。将抗美援朝老兵的物品作为特定人物用品在民俗博物馆进行展陈,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龙泉村的整体性和特殊性;同时,也还原了村落在特定时期和历史阶段的面貌,将村落的人物与发展历程融入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通过具有实在性、历史性的民俗物品展示在作为传媒介质的民俗博物馆中,采取族群叙事策略,对遗存进行了主体性解释和重新创造,建构了爱国主义等符号意义下的村民身份,维系着村落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使村民按照符合村民思维逻辑的方式串联起来,在对外展示中赋予民俗物品以象征性意义,使其成为富有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符号,以此来凝聚群体,强化认同,进而生成新的共同体。”
远景:民俗文化博物馆可持续性发展的思考
本文以宁夏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为微观个案,对民俗文化博物馆作为基层文化机构的实践意义进行了一定的思考,提出了提升博物馆自我表达的发展建议。这在一定意义上为乡村振兴进程中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
(一)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的个案启示
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在乡村旅游及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作为展示村落文化的社会文化机构,其还存在缺乏讲解人员和基础设施配套不全等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以下促进其发展的建议。
凸显教育职能
龙泉村的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理应承担起保障村民文化权益,让村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责任。进一步来讲,应将其发展成村落乡土教育或红色教育基地,让农村适龄儿童及青少年前往民俗博物馆学习参观,将教育范围辐射到周围的村庄及市区,实现其教育、传播和交流的职能。龙泉村村民通过参与民俗博物馆的建设,逐渐增强了文化自信,提高了个人的文化素养。民俗博物馆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应坚持人文关怀,让村民享受到民俗博物馆的文化生活。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应发挥民俗博物馆的文化职能,立足于村民的文化权益,保障村民文化主体的地位,坚持有惠于村民的发展定位。民俗博物馆应承担起传统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的职能,利用馆内展品,提升村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将构建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实践切实融入村民生活中。
更为主动的社区参与
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作为村落旅游过程中展示村落文化的主要场所,博物馆的器物具有承载历史与记忆、文化与传统的作用,故而应将村民纳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队伍中,从而使社区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众多媒体平台,实现对大武口民俗博物馆的线上展示,也将成为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线上传播时,传播内容应尽量真实,从村民的视角出发,讲解民俗物品和在特定时期的生产生活民俗,讲述过去人们在水源、资金、人力等资源稀缺的环境下所产生的民间经验和智慧。在传播主体上,除大武口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官方账号外,还应当鼓励村民注册账号,或在自己原有的账号,发布关于民俗博物馆的视频作品,让村民承担起传播民俗文化的责任。“主体表达的力量和智慧从来不会自然生成或从天而降,它同样要靠无数表达主体能动地表达实践来开创、来持续、来扩展。”
(二)民俗文化博物馆的研究启示
新时期博物馆人类学需要“眼光向下”的“革命”,关注民间,关注传统意义上游离于博物馆之外的那些民间的各种博物馆现象及“博物馆与社区(共同体)之间连接的具体实践”[10],相关研究也需要超越对博物馆的原有认识界限。当前民俗文化博物馆的相关研究十分有限,突出人类学话语和理论的深入研究成果不足,如何看待民俗文化博物馆在当今村落生活中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博物馆应走进群众生活中,其文化意义和价值应基于田野调查,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加以阐释。村民与博物馆物品如何在互动中生成一种新的关系,以及其未来走向如何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民间文化博物馆作为多元文化的展示空间,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社会运动或社会动员,民俗博物馆和区域社会、村落社区的关联应当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村民如何通过乡愁、历史记忆、物质遗存及文化经验等整合共同体内在的联系,民俗博物馆的出现是否是有机共同体重建的需要,这些问题都需要基于田野个案的研究进行回答。
从民俗学和民具学视野来看,在中国社会迅猛发展的村落民俗博物馆及其文化实践正倒逼学术界积极开展对民具学的研究。乡村民俗博物馆中展示的民具成为地方村民与外来游客间的文化互动以及景观再生产的载体。凝聚在民具中的村落历史和集体记忆,如何实现村民的自我表达;如何超越文化展示和文化凝视的简单二分结构,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中通过民具联结的村落共同体实现家园—社区—文化的有效联结与互动,这些都应是乡村民俗博物馆、乡村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特别是文化振兴中重要的实践课题。
参考文献
[1]桂榕.博物馆人类学刍议[J].青海民族研究,2012,23(01):9-13.
[2]杜韵红.新博物馆学视野下乡村博物馆的和顺实践[J].文化遗产,2021(01):102-108.
[3]李潇泉.丁村:一个村庄的沧海桑田[J].旅游时代,2005(06):38-43.
[4]《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编辑部.2015年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5]周星.物质文化研究的格局与民具学在中国的成长[J].民俗研究,2018(04):31-50+158.
[6]郭磊.社会记忆如何可能?[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7]迟燕琼.艺术传承:作为一种族群集体记忆表征的文化实践——以师宗县堵杂村干彝“绑神猴”仪式为例[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9(03):58-65.
[8]孙九霞.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复兴[J].旅游学刊,2019,34(06):1.
[9]彭兆荣.文化遗产学十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2.
[10]尹凯.社区(共同体):博物馆研究中的关键议题[J],中国博物馆,2018(03):20-25.
Tags:#只此青绿